糟糕的cs期中。如果是高中,我糟糕的答案糟糕的结果糟糕的成绩都会化为羽箭,前后上下左右穿进心,不等到成绩揭晓的那刻都拔除不去,一直冉冉地流血,冉冉地自责,红色冉冉的苦痛。现在流不出血了,只有凝结、寻常、被驯化了的身体。考得不好,忘了吧。盼一个curve,差的不仅仅只是我。地球还在转,战争还在打,理想还在远去,糟糕的还会更加糟糕,新的一天总要开始。多疑与敏感匀速驶离我原本吸纳的灵魂,现在它对许多事物产生排异反应——只因为生活在生活之中,这件事本身苦痛得太无法忍受。
Chu二十岁了。“二十岁就意味着人将很难杀。”她说。我愈发相信我们都已越过一个重大的槛,没有越过的人早死在十八岁之前。他们都是贵种流离,大地的污浊和泥泞把稀有娇弱的花骨朵掐灭,粉色、白色、金色的化为箔片洋洋洒洒飘落,为空气掺入许许疗伤。于是野草疯长。或者我们曾经也都是贵种,流离过,然而终究要被磁吸回某种完善的轨道,生的渴求致使曾淋在身上的箔片渐渐脱落,裸露出丑恶、庸俗,和皴裂干燥的土块一副图貌。流离地,那不是家,没有名字,没有记号,没有计算得出的恒稳,不烂漫,不慈爱,不丰茂,不说你好再见,不接受巧工的雕琢,不导航向流离地之外的进出口。虚无,虚无却是真理,真理中才诞生高贵,诞生死在十八岁前、早早与天团聚、与灵合一的人,称作天人。
我不知道人们总体对十八岁给予什么看法和妄想,也许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仪式,毕竟在名为人生的这场漫长的生存仪式中,没有什么会在特定的一朝一夕间消失或者出现。然而我切实感到自己在十八岁的门槛前经历了复生。
这么说便也是经历了死,没有死就没有复生一说。那是六月十五号,我晚上在Lift和加盐与猫喝酒。我点了两杯,第一杯叫什么已经记不清,第二杯是酒吧的招牌叫崂山道士。喝到了那时人生中最醉的一回,我沉重的头颅是一个世界,卡不进视线所捕捉到的昏黑里闪着光点的世界,两个世界分离重影。一起坐地铁回去的路上,我实在受不了,中途某一站下车去洗手间。猫说要护送我回家,于是跟下来。我掏出手机,手机摔进了蹲坑里。捡起来,没有脏。出了地铁站,猫又一路跟着我走过熄灯关门的店铺,似乎有风,似乎没风,夏季序幕那种隐约温热的度量。我说想买一瓶醒酒茶,小区十字路口对面就有一家711,于是我们过红绿灯,我买了一瓶东方树叶,对猫说谢谢你。没有她,我或许还能摸索到家,但不会买这瓶茶。
我推开家门,餐厅灯亮着,照着爸爸妈妈,占据两张乌木纹路的漆黑座椅。我感到惊诧,为自己在酒吧喝的两杯酒微微心虚,醉意不妨碍我意识到他们正在等待我回来。爸爸从冰箱里取出一个蛋糕盒,“庆祝一下。”今天是妈妈的生日。我几乎本能地叫出来:“不用等我啊,你们可以先吃!”妈妈说没事,我看着他们笑,两眼坚定到没有目的地环望,环过天花板、吊灯与家里那些家具、橱柜、沾灰的钢琴。蛋糕脱离了它的禁锢与保护,一根蜡烛给它穿孔,关灯,唱起生日歌,双声调的鼓掌,蜡烛的泪与烟。我有为妈妈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吗?这是她多少岁生日我都算不清楚,从小就算不清楚,也没有计算的欲念,但这都是无所谓的,总归我们共同长久地活了许多年。吃下一块他们切好的蛋糕,聊天,声音嘹亮地回荡。他们去洗盘子,厨房的灯不久灭下,他们和我说早点睡。
呆坐了一会,他们没看出我醉得多么糟糕,至少精神还能清澈自由地发话,甚至比平常更加健谈。踉跄起身,洗漱上床。加盐在微信上说她需要有人陪她醉,我和她说我当然也爱着人,不论人变成什么样,我都不会放弃我的爱,人才不会放弃爱。爱如钢铁,寒光烈烈。那瓶东方树叶被我捏着拿到床头。最后关台灯前,我把剩下不到半瓶全部灌进身体里。世界彻底漆黑了,不论是我、我的躯壳还是外界,我们复原回漆黑的一切。很快非意识的另一半世界也加入我们,梦也融在其中,遗忘与铭记也找到对应的位置。……
我浑身冒汗,惊坐起身,双眼惊恐地瞪圆。不,我想要惊坐起身但没有力气,想要睁眼却只能紧阂。全身都在发热,汗淋淋渗过睡衣,渗进床单,我踢开裹在身上的被子,左右反复翻滚。惊惧的汗,本该着急忙慌点亮屏幕看看现在几点,时间能帮人最快恢复镇定与现实感知。但我知道这是半夜,哪怕人发烧,发汗也通常意味烧快要消退。是这样吗?五分钟,十分钟,人不会永远保持粗重的喘息,汗默默平静下来,心不再剧烈搏动,还在呼吸,应该是那一瓶东方树叶的茶多酚把我刺醒,忘记茶还有这种副作用。我重新预备睡觉,湿涔涔,干燥的风,夜里没有风,夜花费全部身心诉说着夏。夏。
酒。茶。困意。倦意。整理。安宁。抚平。没有苦痛,不会苦痛。睡下。……
再次睁眼,窗外已经有晨光。鸟鸣,垃圾桶里的空塑料瓶,关闭的卧室门。门外拖鞋摩擦地面,他们醒来,劳作,用几十年来积攒的经验应对全新一天的出现,新的太阳。
我意识到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,没有证据,但正是没有证据使得我不断反复坚定这个念头。我意识到此后一切都不同以往,这是重要的锚点,这是追溯的终点与起点,这需要被铭记。我会活下去,我会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,我一定会活下去。
相较于一个月前的成人礼和四天以后生理意义上的生日而言,这更像是我成年的仪式。我开始活一条新的生命,延续之前的肉体与记忆,但不再为过去萦绕的痛苦所牵制。它会源源不断创造出新的痛苦,我可以源源不断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人。随着时间这份力量的源泉要一点点干涸褪色,但就目前而言,它是我意识的另一半,与我在漆黑梦中会合重聚,在流离地边缘驻守眺望,雾蒙蒙的世界。
对于没有死在十八岁前,悲悯哀叹的那部分总会伤感,但总体来说人还是朝着意志前进。我从十四岁起意识到理想灼烧的意义,它放光彩,我从没有用语言界定那理想究竟是什么。后知后觉,我想如果借用文学,多少就可以说明白,说出它闪光熠熠的本质。虽然如今这条生命总归要滚入大地的泥沼,变得丑恶、庸俗,皴裂的土块一般,但毕竟还有再生的希望。毕竟还有难以预知的神谕和启示不畏惧干枯、苦涩,排除千难万阻它们将会降临在干枯、苦涩里,湿润一颗结满血痂的心。我牵绊住这理想,就当命运还在轮转——
爱与真实,如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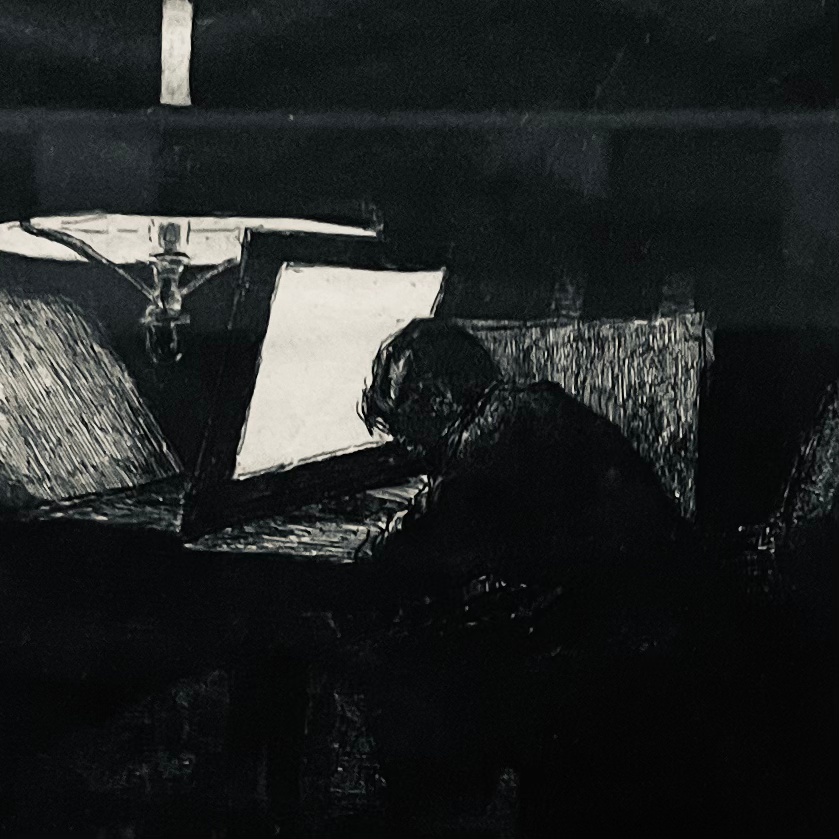
Leave a comment